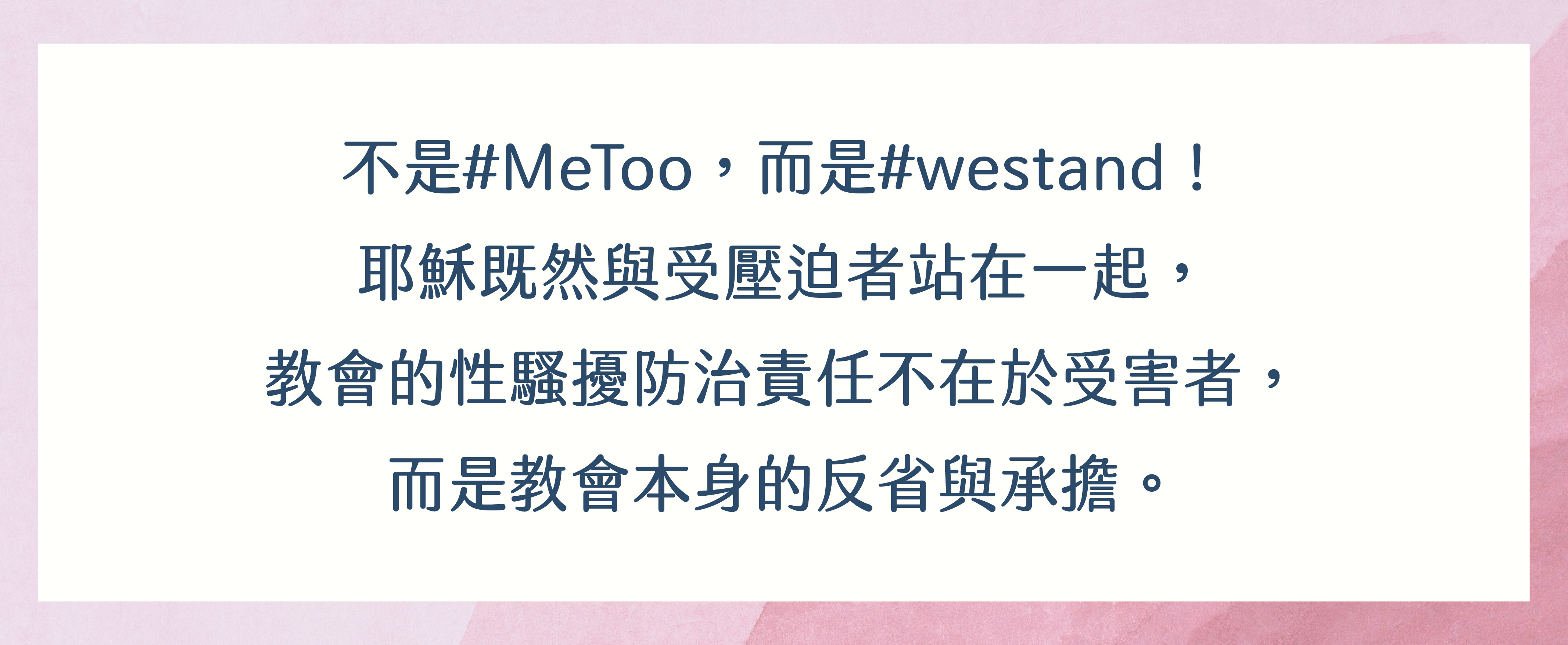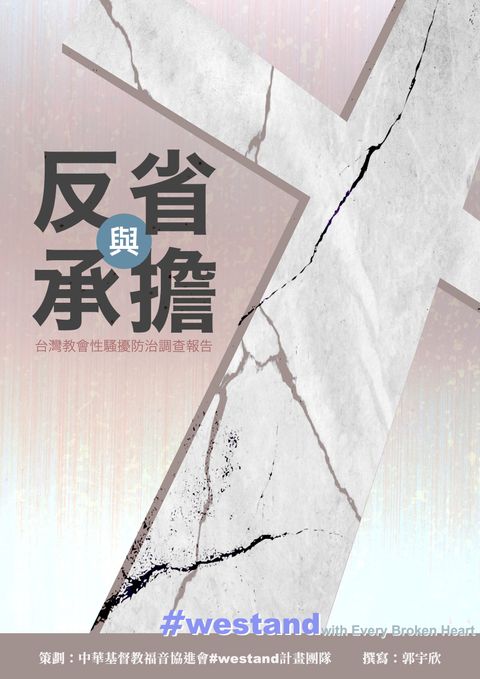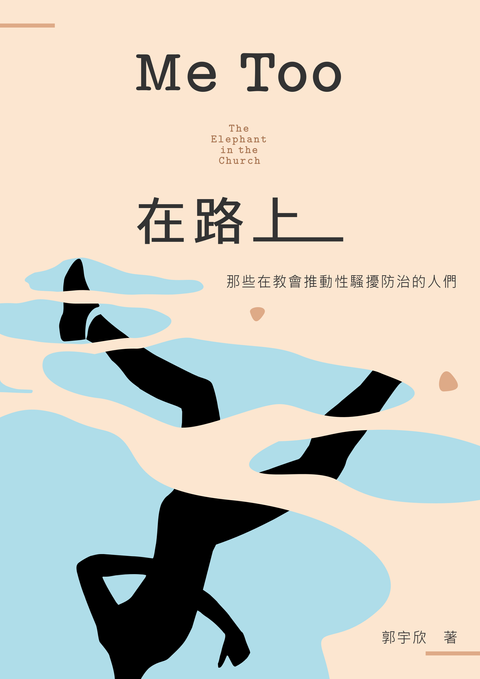文/郭宇欣(葡萄紙文化社長)
2018年至今,我陸續做了幾篇教會性暴力防治研究與報導,也在不同的教會與神學院分享相關主題。我發現,當「教會性騷擾受害者」在講座或耳語中被談論,那些人在沒有遭受性騷擾的弟兄姐妹眼中就成為「另外一群人」,成為「她/他們」。然後,在許多的討論言談裡,我也察覺有些信徒預設的「她/他們」有共同的畫像:女性、信仰不穩定、本來男女界線就不清楚、太過敏感依賴……。但是,我認識一群「她/他們」,有弟兄、有姐妹,熱心事奉、忠心委身、不乏高知識份子,有一些人在生活與職場中聰明幹練,卻因為愛上帝、在意教會群體,而在性騷擾事件歷程中成為最脆弱的一群人,因為在意肢體而選擇隱忍,在乎教會而選擇讓自己受傷。即便受傷,「她/他們」亦沒有把「教會」當成「她/他們」,反而希望教會為自己申冤,希望不要有其他受害者,期待教會與「她/們」站在一起。但現狀卻是,「性騷擾」在教會界仍是一個太具有爭議性、太禁忌的概念,這樣的氛圍讓受害者們默默地選擇噤聲,或離開教會;或隱藏這個故事,繼續參與教會。另一方面,我聽到有的信徒認為性騷擾防治很重要,但似乎只有在教會以外的地方被重視;有的牧者領袖表達這個議題爭議性太大、不知道怎麼做;有的同工想要在教會安排這個主題的聚會,卻被認為沒有必要;有的牧者覺得委屈,認為「性平」預設了牧者都有問題;甚至有的教會內性別事件成為權力鬥爭的武器。
過去社會對性騷擾議題還不太清楚時,性騷擾的受害者被迫背負羞恥污名,好像錯的是受害者。2024年遭遇大規模性暴力受害者吉賽兒(Gisèle Pelicot)提出「讓羞恥感轉向」,認為性犯罪的羞恥感,不應再由受害者承受,而是讓施暴者承擔。而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,作為救恩與盼望的載體,我們能夠為性騷擾防治帶來哪些不同的力量?在香港,因著一位受害者K小姐在媒體投書,協進會性別公義小組開啟了香港第一份教會性騷擾匿名調查計畫;在台灣,因著一位台大校園團契畢業生在天下獨立評論投書,引發#westand團隊進行本次調查計畫。我感謝這些願意為了愛教會勇敢站出來的受害者,而我也呼籲,教會性騷擾防治的責任並不該是由受害者承擔,而是由教會機構本身承擔。
在這份調查報告中,有來自受害者與受害者朋友的沉痛經歷,有來自教會牧者同工與信徒對教會性騷擾防治的觀點與需求。這是一份來自教會的自省,我們自揭罪惡與瘡疤,肯認受害者們的經歷,承認過去在性騷擾事件中的錯誤,呼籲改革的可能。我們知道這段路很遙遠,但道歉與反省是改變的開始,只有教會認為性騷擾事件的錯誤在於自身,性騷擾是內部的權力網絡與性別意識共構下的惡果,而非僅是某個一時衝動或罪大惡極的個人造成,教會才會願意以實際行動承擔這個責任:將這個議題納入同工開會議程、定期舉辦課程培訓、設立預算與專人進行可見的性騷擾防治機制。
或者,有些過去在處理性騷擾事件中亦犯過錯的教會與機構,願意謙卑認罪,願意回頭過來真誠鄭重地向受害者、以及受到影響的信仰群體道歉。
願主使用這份報告內容以及研究參與者的聲音,增進教會對性別暴力議題的重視,轉變教會對性騷擾防治的觀點,願羞恥轉向,願責任也轉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