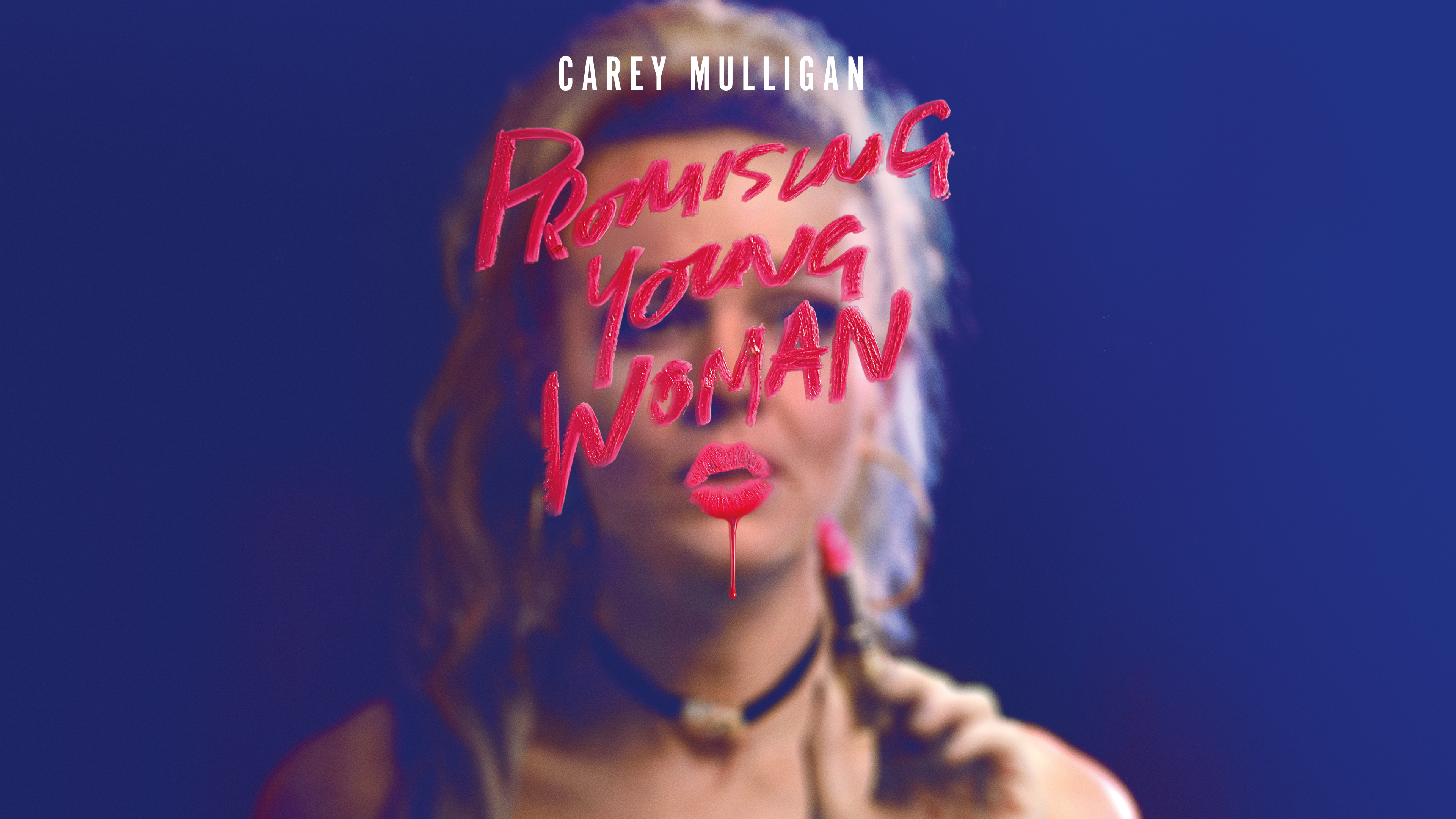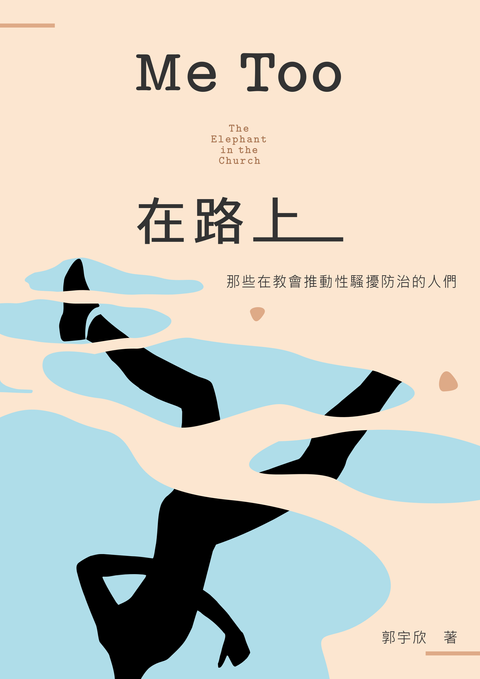文:郭宇欣/葡萄紙文化社長
//受到那種指控,是所有男生的惡夢。那你猜猜看,什麼是所有女生的惡夢?//
——摘自電影《花漾女子》
當女性喝醉時
「撿屍」是近年在台灣媒體中常出現的詞語,形容有人會趁機將醉酒女性帶走性侵,這也是電影《花漾女子》探討的主題。主角凱西(Cassie)的摯友妮娜(Nina)在一次醉酒後被同學性侵,不但好友認為妮娜自作自受,校方也偏袒加害者。結果妮娜在這一連串打擊下自殺,凱西自此從醫學院中輟。凱西開始做一件事,每天到酒吧裡假裝醉酒,而等到她「看起來」酒醉的時候,都會發現此時就會有一個陌生男子看似關心的詢問「還好嗎?」,但實際上是要把她帶回家。
電影原名是《Promising Young Woman》,靈感來自於2015年美國大學裡發生的一起校園性侵事件1,當時法官以「不要毀了加害者前途」而輕判。片中討論為何當女性醉酒時,男性便認為可以為所欲為?為何被譴責的總是受害者?隨著凱西的創傷療癒之旅,我們看到妮娜面對的不只是那一次性暴力,更是存在眾人想法中的強暴迷思,性暴力的發生並不是單獨存在的故事,而是厭女文化下的產物。當施暴者辯稱自己喝醉、暴行旁觀者說自己年紀小不懂事、受害者平時就不符合「好女性」形象時……不但暴行被合理化,也沒有人關注在妮娜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。
在厭女世界裡逆行
彷彿代替妮娜繼續活著的凱西,不像《永不妥協》的艾琳與大集團對抗,也不是女性復仇電影裡讓壞蛋得到教訓的英雄;這個有能力成為人生勝利組的高材生,卻選擇了一條孤獨的窄路,逐一面對在這厭女結構中一個個的「人」。她每晚假裝醉酒被陌生人「撿屍」,在即將被侵犯之際,睜開眼直視對方,清醒的問他:「你要做什麼?」,為何沒有經過她的同意,就認為可以發生關係?凱西透過這樣的行動讓不同的「撿屍者」被迫面對自己的荒謬;讓妮娜的好友體驗斷片後與陌生人同床的驚恐;讓學院院長感受愛女可能被性侵的恐懼……凱西版本的復仇不是以牙還牙,更像是用極端的方式尋求同理和對話。
而作為受害者的妮娜從頭到尾並沒有出現在電影中,呼應大部分性暴力故事裡,受害者的身影總是消失或模糊的;甚至聖經故事也如此,在幾次性暴力事件記錄中,我們僅能聽到他瑪在抵抗性侵時說的話;只得知底拿、利未人的妾不符合當時「好女性」規範;而拔示巴的觀點甚至被省略,直接被敘述成大衛的故事……但她們沒有一個像凱西那樣的摯友,讓人們重新聆聽那些被刪除的聲音。
不想繼續參與遊戲規則的凱西選擇「失敗」卻「清醒」的人生作為抵抗;她正面迎向這世界的惡意,並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。我總覺得,凱西那種活在世界裡卻又不服膺規訓的姿態,與基督徒的生命經驗是何其相似。如果此時當下仍是一個「不合格」女性就該被侵犯的世界,是習慣為加害者找理由的世界……那信仰群體可以有哪些不同之處,使妮娜和凱西們可以被溫柔接待?
電影裡我感受最深的片段是凱西與院長的對話,凱西回憶著妮娜是怎麼樣一個聰明絕頂卻又與她心靈契合的人,這也是我們唯一可以了解受害者的時刻。凱西說「我想如果是你愛的人,那感覺肯定就不一樣了吧。」當一個人被標註「受害者」或任何刻板標籤之前,首先是一個被上主創造關愛、有靈甚至有趣的活人。而一個願意不斷有意識反省性別文化的群體,才有機會與她/他們真正的相遇。
1 相關新聞: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48130
*本文初版曾刊載於香港《時代論壇》2021年6月18日17642期文化版焦點藝評。原標題為《超犀女王》當你迎向這世界的惡意